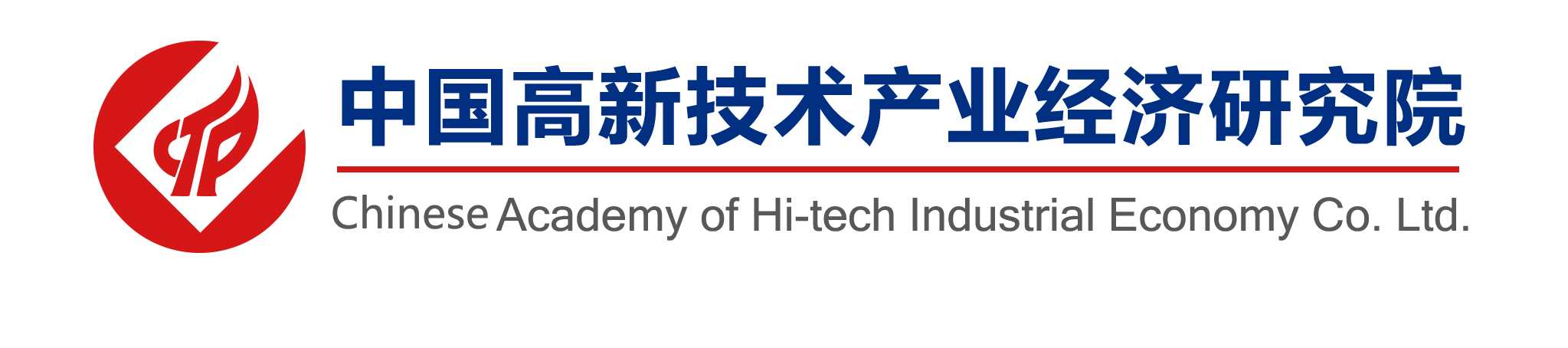吴家骏:中国工业经济学的发展思考
来源:未知 日期:2016-04-25 点击:次
1932年8月出生,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大学学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长。学术专长为工业经济与企业管理。199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著作有:《企业管理漫谈》、《中日企业比较研究》、《吴家骏文集》、《中国企业制度改革研究》、《现代中日经济事典》(共同主编),论文 《探索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道路》等。
坎坷求学
1932年,吴家骏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家庭,兄弟姐妹共9人,家境贫寒。1944年,为生活所迫,12岁的吴家骏小学刚毕业,就辍学到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做童工。1947年,国民党政府按照当时的《童工法》裁减童工,吴家骏得以再次回到学校。为节省学费和追回做童工流失的时间,吴家骏直接跳学到初中第四学期。
吴家骏爱好文艺,中学期间就编剧本、演话剧。1950年离开中学后,吴家骏还报考了北京人艺,只因当年北京人艺只开歌剧和舞蹈班,不招话剧演员,吴家骏才选择了报考财政部办的中央税务学校——他选择税务学校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管吃、管穿、管住,还发助学金,能减轻家里的负担。放弃文艺表演,走上经济管理研究的道路,“也遗憾,也不遗憾”,吴家骏说:“年轻人可塑性强,追求进步的热情高,入学后几场专业思想教育下来,就很快安下心来,学什么都能学得进去。人生的道路也许就是一个在有限选择中发挥无限主观能动性的过程,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要努力把它走好。”
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已经从税务学校毕业,在轻工业部制盐工业局做了5年计划工作、亲身参加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发展愿景规划制定的吴家骏,抱着对国家美好发展前景和对经济工作的浓厚兴趣,在爱人的支持下决定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工经系——虽然这时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吴家骏如愿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60年,吴家骏毕业留校任教。他说:“28岁才算正式走上经济研究道路,我的起步很晚。”
因为中学是跳班上学,吴家骏认为自己的文化课基础没打好,尤其是英语搞成了“夹生饭”,改革开放后要用时却拿不起来。学怕了英语,吴家骏选择学日语——调入经济研究所后,孙冶方所长看到吴家骏这一批青年在大学期间赶上了“大跃进”、“反右倾”等政治运动,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平都较弱,于是决定给时间、给经费让他们打基本功:一是学资本论,二是学外语——不过,刚学了两个月,就赶上了“四清”运动,吴家骏的日语又学成了“夹生饭”。
1990年吴家骏去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在那里要住将近一年的时间,“哑巴日语”怎么行?那时吴家骏已经58岁,他托人按特例进入了一个专为18岁青少年出国前强化口语的培训班,“刚学了两个月,签证下来了,又是个‘半拉子’”。在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完成研究任务后,吴家骏用中文写了5万多字的论文,照例要在研究所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要点,他委托别人,用汉字将自己的论文提要用日语读音标出来,硬着头皮用日语去讲,“讲了半小时,满头大汗,估计别人也没听懂我在说什么,但会场鸦雀无声,他们用鼓励、友善的目光看着我,讲完后还报以热烈的掌声,我是又兴奋、又惭愧。”
追随大师
吴家骏在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起步阶段遇到了两位经济学大师,一位是马洪、一位是孙冶方。两位大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敢于发表有突破性观点的理论勇气,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1960年,吴家骏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就被借调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直接接触并对他影响深远的人是马洪。“马洪思想敏锐,对实际了解透彻,理论概括能力强,每一个历史转折时期、每遇到一个重大事件,他都注重从调查研究入手。”吴家骏说。为了起草“工业七十条”,马洪在北京组织了十家企业进行调研,并到北京第一机床厂蹲点半年,吴家骏被派到京西煤矿蹲点。他回忆说,在调查中听到工人反映劳动强度大、时间长,得不到充分的休息,而企业领导却说他们非常注意贯彻8小时工作制,不允许加班加点。面对完全相反的说法,到底如何判断,他们按照马洪的指示,通过与矿工同吃、同住、同劳动,精确地查定工人从早到晚的劳动时间和休息时间。当时的矿工多为附近的农民,住职工宿舍的外地矿工很少,他们对工人上下班走路或骑车的时间、排队买饭和用餐的时间、排队领矿灯和还矿灯的时间、上下井排队等罐笼的时间、到了井下走巷道的时间,甚至上井后排队洗澡的时间等都作了精确的记录。最终发现,工人们下班后的空闲时间的确很少,睡眠不足,很难保证恢复体力。这样深入细致的调查,为企业改进管理、缩短辅助时间、减轻工人劳动强度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通过这次系统的调研,不仅使吴家骏领悟到了马洪治学精神的核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而且也使他学到了调查研究的本领,树立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学风。
1962年,吴家骏正式调入经济研究所,又直接接触了孙冶方。孙冶方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领导下的经济研究所不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上有很多建树,对实际经济建设工作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他的领导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成为经济研究所的一大特色。吴家骏在经济研究所工作期间,跟随孙冶方到大庆油田、长春汽车厂、富拉尔基重机厂、吉林化工厂、丰满水电站以及大兴安岭林区等很多企业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研究的体验,使吴家骏受用一生。孙冶方虽然是研究理论经济学的,但对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的实践活动也非常重视。孙冶方在那个时期提出过很多震动很大的突破性观点,例如,经济工作要“牵牛鼻子(指抓利润指标)”,不要“抬牛腿”;企业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是“复制古董(指设备大修理基金的使用,只准照原样恢复,不允许结合大修对设备进行改造)”,妨碍技术进步等高论,都不是靠“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调查研究产生的真知灼见。跟随孙冶方工作的时间虽然只有两年多(其后孙冶方便遭批判),却对吴家骏一生的研究风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他深深地感悟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参与主编《现代中日经济事典》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生效,邓小平访问日本圆满成功,日本掀起一股“中国热”,两国间经济学术交流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学术交流中,中日双方共同感到存在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由于两国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体系完全不同,相互很难准确理解对方的经济概念和经济事件,经常出现误解和误会。在两国经济界交流中,同样的问题和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情况,往往需要反复介绍,效率很低。中日双方都需要一本“入门书”来方便沟通。
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和日本国土厅顾问、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理事长下河边淳共同主持的《现代中日经济事典》开始编撰。事典分两册,一册是面向日本读者的《现代中国经济事典》,由中方撰写、日方翻译,用日文出版;另一册是面向中国读者的《现代日本经济事典》,由日方撰写、中方翻译,用中文出版。《现代中国经济事典》的编辑委员会中,主编是马洪,副主编就是吴家骏。
《现代中国经济事典》阐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基本情况,并按照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分章节、条目,其涉及面包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介绍了农业、工业、商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主要经济部门的基本情况,阐述了国家有关计划、财政、金融、物价、劳动工资、基本建设、对外经济合作等政策和基本程序。总之,读者通过阅读《现代中国经济事典》,可以比较系统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概况,也可以说,这是一本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入门书”。吴家骏说:“《现代中日经济事典》对促进中日经济学术交流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要想全面系统地了解日本经济、全面系统地了解我国计划经济体系下经济运行的机制和改革初期机制转换的情况,它仍然不失为一部很好的参考书。”
以《现代中日经济事典》的出版为契机,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和日本综合研究所议定,联合举办定期的“中日经济学术讨论会”,在中日两国轮流进行,从1983年开始到2001年1月,共举办了7次讨论会,讨论会围绕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进行研讨,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作为中方会议组织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吴家骏为这一交流活动作出了主要贡献。
工业经济与企业管理研究
吴家骏的研究领域一直很集中,他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致力于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理论与实际问题研究。20世纪60年代初,在起草“工业七十条”企业调查的基础上,马洪主编了《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一书,吴家骏撰写了部分章节并参加了全书的统改和定稿。“文革”结束后,吴家骏深入研究中国企业管理落后的原因,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改变企业管理落后面貌的对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酝酿改革开放大计,胡乔木提出一个“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课题,马洪领回一些研究任务,其中一项就是企业管理与企业改革。马洪带着吴家骏到北京东郊红星养鸡场作调查,总结该场解决人浮于事、改变企业“小而全”的经验,写出了《红星养鸡场调查》一文,用实际案例论证了只有用经济办法才能解决企业存在的种种问题,通过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内部刊物《经济管理通讯》上报。
1978年9月9日,吴家骏和马洪一起用 “马中骏”的笔名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一文,强调“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应当把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作为基本的出发点”、“要承认企业在客观上所具有的独立性,赋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这是一篇较早触及企业性质、地位和自主权的文章,对推进企业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吴家骏参加高层访日团考察日本企业,向中央反映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对改革开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和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合著的《访日归来的思索》一书被誉为“改革开放初期工业领域和科学管理领域的开山之作”。
1980年,吴家骏在《红旗》杂志等刊物发表了《探索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道路》、《论管理科学的发展和现代管理的特点》等文章,强调“实现管理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吴家骏对中国企业问题的研究比较具体和深入,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包括:
(1)研究借鉴日本企业的组织结构和动力机制,探索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1990年—1991年,在考察日本股份制企业和证券市场的基础上,完成了《中日企业比较研究——日本企业的组织结构、动力机制与中国的企业改革》的研究报告,并通过一系列文章,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总体构想。马洪在《吴家骏文集》的序言中说,这些文章“比较早地提出了在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过程中,通过企业法人相互持股实现股权多元化、分散化的主张……”。
(2)研究现代企业制度,强调“有限责任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特征”,主张“深化企业改革要在有限责任上下功夫”。1993年底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任务后,针对学术界流行的一种把现代企业制度简单等同于公司法人制度的观点,吴家骏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指出这种观点是不确切的。他认为,“有限责任是两权分离的根本前提,是现代企业一系列制度特征的总根子”。这些论述在当时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
(3)研究如何增强企业活力,提出“企业活力的源泉主要不在所有制形式而在合理的利益结构”的观点。针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的问题,吴家骏提出“在研究和探索企业活力源泉问题时,不宜把企业所有制问题的地位和作用看得过重、过高”。通过对各国现代企业实态的分析,他认为研究企业活力的源泉,最重要的是利益结构而不是所有制。提出“需要对所有制的认识进一步解放思想,要从利益关系上寻找企业活力的动因,要把侧重点从所有制问题转移到利益关系调整上来”。
(4)研究和运用企业形态理论,分析阐明国有企业民营化同私有化的异同。针对民营化和私有化的关系以及股份制企业“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争论,提出民营化不等于私有化。他认为民营化是经营形态范畴的问题,股份制是法律形态范畴的问题,而私有化是经济形态范畴的问题,三者并不是一回事。从国际经验来看,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可以伴随所有权的改变,但在多数情况下和所有制的变化无关;股份制可以是私有的、可以是混合所有的,也可以是公有的。把民营化和私有化等同的观点是把经营形态与经济形态混淆了;说股份制“姓资”还是“姓社”,是把法律形态与经济形态混淆了。这些观点对于解决当时困扰我们的关于民营化和私有化的关系问题,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5)研究公司治理的国际经验,提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思路。他认为在公司治理结构研究中有三种值得注意的倾向:脱离开企业产权制度空谈治理结构的倾向;脱离开合理的利益结构孤立地强调维护所有者利益的倾向;笼统地反对内部人控制忽视“败家子”控制的倾向。
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中国工业经济学的发展
吴家骏一直致力于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理论与实际问题研究,对新中国“工业经济学”经历了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过程,感触颇深。“改革开放后,作为二级学科存在了几十年的工业经济学却在学科分类目录中被一笔勾销,致使高等教育中的工业经济专业不再有立身之地,随之销声匿迹,其现象值得经济学界深思。”吴家骏说。
新中国成立之前,工业水平落后,也没有工业经济学,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前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开始有了现代工业,相应地也从前苏联引进了工业经济学,而这个学术基地,就在中国人民大学——按照前苏联模式设立了工业经济学专业,随后,全国财经院校也纷纷设立了工业经济学专业,主要教授的内容是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在引进工业经济学的同时,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吴玉章一直强调,要将前苏联的教科书“中国化”,但因为“文革”的影响,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文革”之后恢复高考,工业经济学专业也开始招生,如何尽快编出专业教材成为当务之急。
1978年6月,在陕西财经学院刘廉生等人的倡议下,编写工业经济学教材的活动得到时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洪的支持。1978年10月工业经济学教材编写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廉生、王祥春、黄德鸿、李永禄、刘敏世、董守才等人参加了会议,作为社科院工经所的代表之一,吴家骏也参加了策划。与会者希望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牵头组织教材编撰的攻关,马洪欣然应诺,并提出教材编写的两个要点:一是企业是工业的基本单位,研究工业经济必须从企业入手。二是针对当时经济工作混乱的局面,强调研究工业经济必须同改善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因此,工业经济教材也更名为《中国工业经济管理》。1979年6月,《中国工业经济管理》初稿讨论会在上海举行,并组成了以社科院工经所陆斐文、曾延伟、吴家骏和上海财经学院顾理为主的编委会。1979年11月《中国工业经济管理》作为工业经济学的试用教材在上海出版。1985年,修订后的《中国工业经济管理》经教育部审定成为“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并于1991年获得“光明杯”荣誉奖。
改革开放后,西方经济学逐渐成为显学,但西方经济学中并没有工业经济学之说,取而代之的是产业经济学。到1997年产业经济学被确定为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之后,各高等院校为解决教材需求,纷纷开展产业经济学学科建设,编写产业经济学教材,各类公开发行的教材发展到几十本,虽然体系各不相同,但基本上还是沿着东西方的宽窄两派的思路展开。窄派认为,产业经济学就是产业组织学,而理论、方法都已成熟;而宽派则认为,产业经济学不只是产业组织学,它是研究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以及产业政策等的新兴学科。
随着产业经济学研究的兴盛,工业经济学却逐渐式微。2005年中国社科院工经所所长金碚在《新编工业经济学》一书中感慨:“当中国进入工业化的加速增长时期,工业经济正展示其极大地改变着整个社会和国家面貌的巨大能量,发展工业成为几乎所有地区的发展战略重点的时候,而且就在探索如何走新兴工业化道路正在成为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重大课题的时候,工业经济学却表现式微,面对红红火火的工业经济发展的现实世界,工业经济学却似乎给人以退避三舍的印象。这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个遗憾。”
吴家骏认为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并不是工业经济学者固守原来的观念跟不上改革开放的步伐,也不是工业经济学无法与时俱进地适应市场化改革的需要,而是教育部颁布的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引导的结果。1997年教育部颁布新的学科分类目录,在二级学科中取消了几十年来我国一直沿用的“工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学科,新设了“产业经济学”。很快各高等院校就按照这个分类目录的指引,取消了工业经济系和专业,不再招收本科生、研究生,授予学位的学科也都改成“产业经济学”。
“一门学科是否能够成立首先取决于是否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工业经济学在学科分类目录中被取消,并不等于工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消失。而工业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客观地存在于现代工业发挥在过程中的经济规律,并探讨在不同具体条件下,自觉利用这些规律的途径和方法。”吴家骏说:“中国教育的目的绝对不应是让受高等教育者的注意力离开生产一线,特别是离开农业和工业的生产一线。现在中国工业发展正面临着教育方向与经济发展之间结构性偏离的矛盾。历史的经验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相关文章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