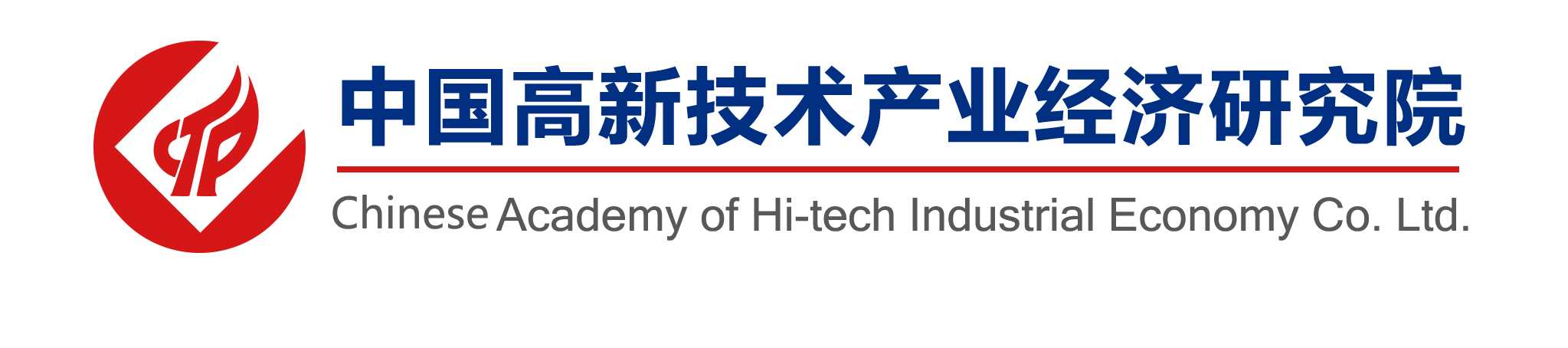增长极概念的演化与区域发展重点的转变
来源:未知 日期:2016-10-25 点击:次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发区域发展新动能,拓展经济新空间,培育新的增长极,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经济空间格局、推动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战略工具。无论是实施均衡发展战略还是非均衡发展战略,无论是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还是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国家和各级政府制定的规划和文件中,将某个城市、城市新区、产业集聚区乃至整个城市群打造成新的“增长极”,已成为我国空间规划最为常见的战略表述。但是,究竟什么是增长极?培育增长极需要什么样的基本条件?增长极概念的内涵及其实施的战略重点随时间发生了哪些变化?本文拟从增长极概念与战略重点的演化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阐释和论证。
一、作为推进型企业的增长极
1955年,法国经济学家F.佩鲁(FrancoisPerroux)首创增长极概念。他认为,“增长并非在各个地方同时出现;它首先出现于不同强度的增长点或增长极上;并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对整个经济体产生不同的终端效应”。作为经济学家,佩鲁观察到,经济空间是由中心或极、焦点组成的,这中心或者极,本质上是指推进型企业。首先,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增长是不均衡的,存在极化发展趋势;其次,这种极化是由技术创新推动的,而技术创新是由推进型企业实现的;第三,具有创新技术的推进型企业的形成和集中需要特定的环境;第四,推进型企业与其前后生产关联的企业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力场,并由这种力场形成该企业的经济空间;第五,在推进型企业的经济空间中,相关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等的,即推进型企业支配其它企业;第六,增长极通过推进型企业的力场,来实现其在经济空间中的扩散效应,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因此,当我们溯源增长极的概念时,一定不能忘记,增长极的核心主体是企业,特别是具有创新技术的推进型企业。当某一城市或区域要培育和打造增长极时,要将培育和引进具有创新技术的推进型企业作为战略重点。
二、作为主导部门的增长极
1958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A.0.Hirschman)在其《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不平衡发展理论。他强调,发展路径是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战略就是集中有限的资金,选择具有较强产业关联度的某一类或几类主导产业部门进行战略投资,通过产业的前向关联、后向关联和旁侧关联等连锁效应,带动其他部门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的起飞。显然,赫希曼的不平衡发展战略,本质上是同佩鲁经济空间不平衡增长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他注意到,要实现不发达地区经济的起飞,仅仅对个别企业进行投资是不行的,只有在产业联系效应强的若干主导产业部门进行战略性投资,才能为经济的起飞创造基本的条件。与佩鲁强调推进型企业的技术创新相比,赫希曼则更强调产业的连锁效应。他认为,如果主导产业部门的投资由政府来做,应优先选择社会成本低、外部经济好的公共部门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来进行;如果是私人资本,则应投入到带动作用强的制造业部门。因此,当我们运用增长极概念和战略时,一定不能忘记,增长极的培育和打造,关键是要选对主导产业部门并对其进行战略投资。同时,也不能忘记,若增长极的培育和打造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其主导产业部门应选择基础设施建设;若主要依赖私人投资,则应选择产业关联度高、产业带动能力强的制造业部门。
三、作为增长中心的增长极
佩鲁、赫希曼等经济学家,虽然在增长极概念的建构中,也注意到地理空间的不平衡性,但在他们的眼中,地理空间不过是经济空间在地理上的投影。法国经济学家J . R .布代维尔(J.R.Boudeville)在区域经济规划研究中,就明确将佩鲁等抽象的经济空间转换为具体的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的运用;由于外部经济和集聚效益, 形成增长极的工业在空间上集中分布, 并与现存城市结合一起。由此,“增长极就是城市增长中心,该增长中心的增长可以向周围地区扩散”的观点,与上世纪60、70年代地理学计量与理论革命对城镇体系的关注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增长极的推进型企业和主导产业部门的指向迅速转向城市增长中心的指向。相应的,增长极理论和战略,也迅速成为区域发展战略和空间规划最核心的理论和政策工具。但是,由于在区域城镇体系发展演化中,不同类型、功能、等级的城镇,其发展条件、基础和潜力差异很大,将城市增长中心作为增长极来选择和培育,往往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等级中心城市容易取得成功,而在经济落后地区和低等级城镇,则易遭受失败。究其原因,城镇虽然作为经济活动的集聚空间,其核心支撑仍是企业和产业。如果一个增长极缺乏创新性、带动性强的推进型企业,如果支撑增长极的企业不能发展成为富有竞争力的优势主导产业部门,那么这个增长极战略失败的风险就很大。因此,将城镇中心作为增长极,是有条件的,关键还在于能否针对某一城镇在城镇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和发展条件,培育和吸引一批创新性、带动性强的推进型企业,并围绕推进型企业培育发展产业集群,进而形成富有竞争力的优势主导产业部门。
四、作为流空间节点的增长极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彻底重塑了城市以及城镇体系的概念。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通过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和生产活动的片段化,实现了经济活动在地域上的高度分离和空间集聚;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公司和跨国家组织所构建的全球生产网络,又实现了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高度整合。这样,城市特别是高级别的国家中心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不再是相互分离的孤岛,而是通过各种流而相互紧密联系的无边界网络。在此背景下,城市和城市区域作为传统的“地理空间”,已被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所形成的“流空间”所重塑,城市和城市区域不仅仅是区域要素和经济活动集聚的场所,更是人员、货物、金融、思想、技术、知识等跨区域和跨国流动的节点和枢纽。于是,一种新的城市形态——全球城市应运而生,这些城市演化成为全球和跨国经济的指挥控制中心、金融和信息服务中心、科技和教育创新中心、文化创意和消费中心。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使地理空间变得更加润滑,如何打造“粘性”空间、提升特定城市或城市区域在流空间中的抛锚能力,就成培育和打造增长极的一个新的时代课题和战略取向。这样,上世纪60、70年代作为地理空间增长中心概念的增长极,就演化成为在流空间中的网络节点和枢纽。显然,在增长极的战略定位上,传统的国家之下的区域尺度已无法体现城市和城市区域发展的诉求,跨国和全球尺度的分析才能凸显高等级中心城市的价值。同时,为更好应对经济全球化,强化区域的粘性作用和抛锚能力,另一种新的城市形态——城市群或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也广泛出现。这样,作为流空间节点的增长极概念,不仅仅指单一的某个城市,也经常用于指众多城市在特定地理空间的集聚——城市群。将我国中西部地区一些重点城市群打造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带动中西部地区转型发展的新增长极,也就自然成为目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点方向。
五、作为创造场和学习场的增长极
同样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全球化的推进、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催生了新增长理论和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兴起。与上世纪60、70年代依赖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下增长极的选择和培育不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以新增长理论、制度和演化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新区域主义,更加强调城市和区域的内生性发展,倡导自下而上的政策行动,主张政策的关键在于增强合作网络和集体学习,将地方化的投入产出联系和学习创新作为城市和区域竞争力提升的关键,由此形成了将城市、城市区域看作是通过新企业形成、技术学习与创新的“创造场”、“学习场”来实现增长的增长极概念。
新区域主义认为,凯恩斯国家干预下的增长极战略,对落后地区而言,本质上是在“依赖发展”和“不发展”之间进行选择。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所创造的新的竞争形势下,只有通过营造优良的环境,提升城市、城市区域的集体学习和网络建构的能力,才能实现“内生性发展”。对发达国家而言,城市和城市区域的增长依赖于创造场的培育发展。美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斯各特(A. Scott)认为,“创造场”可用于描述任何塑造或影响创新的社会关系系统,它是创新相伴发生的场所,这种创新的生成是一个社会和空间嵌入并随时间而演化的现象。“创造场”本质上是企业家、创意阶层与城市区域集聚经济的互动过程,是新经济在特定地理集聚空间中的循环累计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创造场”概念的核心是地理集聚而非学习创新,因为它假定地理集聚本质上就是一个分享外部经济同时促进学习创新的过程。
以“创造场”概念为基础,我们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和“技术-组织-地域”三位一体的分析架构,提出了更具有普适性的“学习场”概念。我们认为,创新的本质是个人、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多样化的行动者在多种尺度上交互学习的过程,该过程依赖于地理接近、关系接近和制度接近在特定时空情景的有机结合,依赖于地方网络与跨区网络的战略协同。与“创造场”更多强调集聚不同,我们的“学习场”概念更加强调学习,并将创新过程被视为嵌入于社会和空间的互动学习过程。城市和城市区域要成为增长极,营造由支撑和促进交互学习的制度、文化、社会结构等在内的社会关系或网络系统所组成的“场域”,是培育和打造增长极的基础条件;而以“场域”为基础,塑造良性的、制度化的“惯习”来保证学习的有效进行则是增长极培育和打造的核心。与作为流空间节点的增长极概念一样,作为学习场的增长极概念不仅仅用于指单个城市,而且也经常用于指城市群。打造创新型城市群,将城市群打造成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的创新中心,也已成为我国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
综上所述,从增长极概念及战略重点的演化来看,上世纪50年代的增长极理论侧重于经济空间中的推进型企业和主导部门,60-70年代的增长极规划侧重于地理空间中的城市增长中心,而80年代以来的增长极战略则侧重于流空间的节点和学习创新赖以发生的创造场和学习场。增长极概念的这种演化轨迹,体现了城市与区域发展理论和政策的4个重大转变:在空间的认知上,从抽象的经济空间转向实体地理空间,进而进一步转向流空间和创新空间;在分析的尺度上,从具体的推进型企业、主导部门到单一的城市或城市区域增长中心,进而扩展到由多个城市地理集聚所形成的城市群或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在增长的源泉上,从战后新古典增长理论所强调的要素投入转向新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创新驱动;在战略的导向上,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下的依赖发展转向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内生性发展。综观增长极战略在战后以来的政策实践,要保证增长极战略和政策的成功,增长极本身的科学选择以及其战略重点的有效确立和实施非常重要。在增长极的选择上,应将增长极看做是由推进型企业、推进型企业所在的主导部门、主导部门所在的城市增长中心、城市增长中心所在的流空间节点、流空间节点所嵌入的创造场和学习场等所共同组成的复杂经济系统;在增长极战略重点的确立和实施上,应以明确增长极在流空间中的功能定位为前提,以营造创新场和学习场为基础,以提升学习创新能力为核心,以培育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为抓手,着力提升增长极在流空间的粘性作用和抛锚能力,发挥城市增长中心的集聚效应,大力培育和引进具有创新技术的推进型企业及其关联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