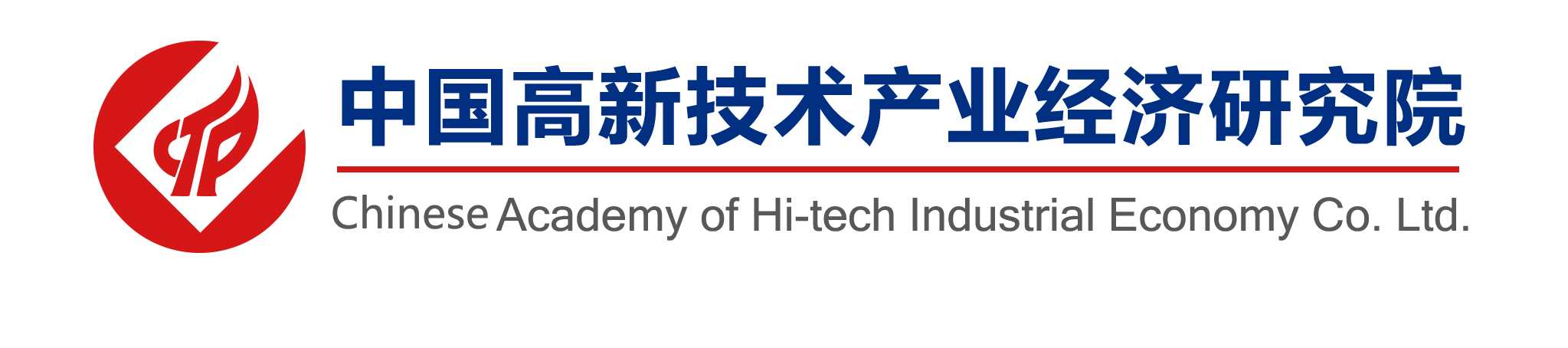区域经济“分化”的含义及政策选择
来源:未知 日期:2016-04-28 点击:次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在后金融危机的持续震荡和复苏蓄能阶段,国际经济的周期性转折与国内经济的结构性调整相互叠加,导致中国经济开始步入增长速度下行、增长动力转换的新常态。2010-2015年中国GDP增长率已经从 10.63%持续下降至6.90%,经济体量的增大、域外格局的波动和内部的转型使命,共同引致中国整体确立了从超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基本趋势。
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及阶段性特征并不一致,这意味着整体经济走向在不同地区往往具有明显的差异化“投射”。如果观察整体经济下行中的区域增长格局,则可以发现: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分化特征渐趋加剧,2013年-2015年31个省区GDP增长率的变异系数已经从1.443攀高至1.760。
此外,从东部(共10个省或直辖市)、中部(共6个省)、西部(共12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东北(共3个省)这四大区域板块来看,经济业已呈现出“东部缓慢回落、东北快速下行、中部和西部持续高速”的复杂图景,2015年中国东部除天津、江苏和福建之外,其余7个省区的GDP增长率均低于或等于8%,其中北京和上海均为6.9%;中部除山西(增长率为3.1%)之外,其余5个省区的增长率均高于8.0%;西部除内蒙古、四川、陕西和宁夏之外,其余8个省区的增长率均高于8%,重庆、西藏和贵州甚至分别达到11.0%、11.0%和10.7%;东北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增长率分别为3.0%、6.5%和5.7%,均下跌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最低点。
上述地区经济分化格局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组成部分,因此也应基于整体经济格局和区域经济特征的交互作用进行审视。
在经济新常态格局下,不同地区均面临着发展动力机制转换的核心命题,然而禀赋条件和发展阶段的差别又导致各地经济“转型”的内涵和指向迥然不同,这种差别是引致区域经济增长率出现分化的决定因素。东部地区居民收入率先步入国际标准界定的中等收入行列,产业结构则整体步入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例如:2015年北京和上海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9.7%和67.8%。这种情形意味着东部地区的各类要素成本在持续走高,而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空间也渐趋下降,因此其转型的核心是促使经济增长从要素密集投入类型转向要素组合效率提升类型,换言之,由企业创新和劳动者人力资本提高等所引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将在东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就此而言,从要素密集投入向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转换、以及转换进程中的适应性调整是导致东部经济缓慢回落的基本成因。与此相对,东北经济则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矿产资源和农产品(12.30, -0.06, -0.49%)供给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两种资源的价格波动很容易对东北经济发展产生冲击;二是作为承继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庞大的国有经济体量以及由此衍生的国企转制成本也成为影响增长的重要因素,这样东北面临着产业结构从过度依赖资源部门转向产业多样化、产权结构从过度依赖国有企业转向产权多元化的双重使命,这两种转型的相互叠加、以及转型与现有制度之间的失配是导致东北经济急速下滑的基本原因。
在中国经济增长整体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中西部获取了此前东部地区高速增长的“接力棒”,这种格局首先是因为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多数省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基数较小,且中西部在劳动、土地等要素禀赋中具有价格优势,进而基于产业结构梯度转移形成了多种类型的产业集群(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更值得强调的是,中西部整体上处在工业化的起飞或加速发展时期,且政府对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也在持续发力,这些格局意味着中西部的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以政府投资进而营商环境改善为牵引力,通过充分利用已有的要素比较优势来加快推动工业化进程,投资增长、要素使用以及与东部地区的错位发展,是现阶段中西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源(14.090, -0.29, -2.02%)泉。
作为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区域经济分化显然具有多个维度的引申含义。不同地区的增长绩效既取决于整体的国际国内经济走势,也导源于各地的结构特征及其转型使命,因此,经济制度和政策选择应关注这种空间“异质性”特征,试图采用行政手段去“干预”区域经济分化很可能难以真正奏效。进一步地,区域经济分化是“嵌入”在各地的经济特征之中,这暗示着这种分化很可能伴随着结构特征演进而延续较长的时间。
长期来看,区域经济增长从分化走向收敛将主要取决于如下因素:中西部整体步入后工业化时期并由此导致增速回落,东北地区有效推进了产业—产权结构改革进而导致增速抬升。这两者均难以一蹴而就,也难以一路坦途,这暗示着:在四大板块的增长率意义上,区域经济分化是区别于此前情形的一种“新常态”。相对于国际金融危机初期,现阶段区域经济分化是在更多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情形下发生的,它从侧面显示:反思并放弃了依靠普遍化、高强度的政府刺激来驱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方案。
与传统方案相伴随的往往是各地的增长动力来自政府大规模投资,增长绩效则呈现出向高速度的趋同,这种情形可以带来整体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区域经济增长收敛,但也通常伴生着产业结构同构、产能严重过剩和政府债务压力攀升。反过来说,现阶段的地区经济分化是矫正此前经济刺激方案、真正实施转型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表征。
如果说区域经济分化是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并且体现了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趋向,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分化与统筹地区发展之间的关联?进一步地,什么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政策选择?如前所述,现阶段的区域经济分化主要表征为不同地区增长率的发散,而统筹地区发展则主要表征为不同地区的要素具有大致相同的回报率、以及不同地区的居民具有大致相同的收入水平。
显而易见,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走向收敛是统筹地区经济发展的最终指向,而经济增长率的空间特征是实现此目标的工具因素。这意味着:在要素流动性增强的前提下,不同地区的增长率分化和居民收入收敛是可以并行不悖的。由此出发,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政策选择就是:首先,理性认识区域增长率分化的成因及其经济含义,不应将这种分化直接等同于地区经济差距的加剧,进而采取政府干预举措或普遍化刺激方案去实现增长数字的“趋同”。
其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在市场化改革条件下,主要依靠商品-要素的跨地区、跨产业、跨部门流动而实现的,考虑到商品—要素流动的空间范围在不断拓展,则应重视不同板块内部的要素配置效率(例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战略),更应关注不同板块之间的要素配置效率。在这个意义上,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等战略应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原因在于这些战略相对于中部崛起战略等具有更突出的跨空间板块特征。
第三,无论是就东部、中部、西部还是东北而言,其实现各自的经济转型目标均依赖于市场化改革(尤其是要素市场化改革),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价格机制会导致资源优化配置,从而推动不同区域投入结构、产业结构、产权结构、需求结构等的顺利转化,据此应将市场化改革的重点放置在要素市场化维度,在推进要素产权制度和交易制度完善的基础上,为各类要素发现并自发配置到高回报部门提供有力保障,这是中国整体回应各类经济挑战、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立足点。
最后,区域经济发展还涉及政府经济职能转变以及调控效力的提升,例如:东北地区的经济急速下滑与其承担的资源供给目标紧密关联,而资源供给往往具有某种程度的“准公共产品”性质。由此出发,中国应在深化财税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改善区域经济关系,例如:通过甄别跨地区“准公共产品”供需对接程度来确立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此外,还应完善纵向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厘清不同层级政府的经济职责、支出结构和财政收入规模,通过财权适度下沉和事权适度上移化解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收支缺口,进而为不同区域的经济转型以及协调发展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
相关文章推荐: